阅读:0
听报道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有人返乡,有人旅行,也有人哪儿都不去,在家休息、读书。资先生也在旅途中。翻出一篇资先生重游维也纳的旅行文字,在年关之前分享给大家,顺祝朋友们新岁吉安!春节假期,将停更两周,至2月26日(正月十一)恢复更新。——小编
重游维也纳之一
访旧得旧的惊喜
文|资中筠
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工作关系在维也纳住了三年,自1959年回国后再无缘重访,最近到巴黎探访女儿一家,蒙他们为满足我怀旧之情,安排了维也纳之行。过了半个世纪旧地重游,最大的惊喜是访旧得旧。
国人已经习惯于“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总是以“变”为主调。隔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国人总是惊叹简直认不得了,作为对主人的恭维,于是主人也以此自豪。与此同时,各大小城市争相“与国际接轨”,千篇一律、杂乱无章的高楼林立,结果使人不知身在何处。
一
这次一到维也纳令我惊叹的却是面目依旧,宛如昨日。那一条条小石块铺路的小街,那一排排高不过五、六层,蓝、白、黄色粉墙,红瓦屋顶的民宅,还有大街中心的有轨电车,都依然如故,既没有刷新,也不显破旧。不过电车的车厢看来大部更新过,座位比较宽敞舒适。说半个世纪不变,其实不准确。
维也纳城市建设过程我没有仔细研究,至少可以说,我半个世纪以前到来时城市基本规模和面貌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特别是二战最后苏军的轰炸,战后重建基本上按原样修复。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战后初期为应急而匆忙建起来的民宅,虽然形式还是沿袭原来的式样,没有高层建筑,红瓦盖顶,只是外墙全是水泥色,多少年也没有粉刷,使人一望而知是战后50年代的产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不盖“现代化”的高楼,不过都集中在原来属于郊外的另一个区,称“联合国城”,是国际中心。在市内我只见到过一幢大约有二十几层高的玻璃盒子形的高楼,是世界许多城市都有的“国际饭店”,这“鹤立鸡群”的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把一条街“破了相”。据说当地人也认为这是失误,从那以后再不允许在市内建这种楼。偶然也见到无处不在的麦当劳快餐店,但也是藏在与那些咖啡馆一样的古色古香的门面内,那个“M”字母也收敛得小一些,不那么张扬。
当然,和许多欧洲历史名城城一样,作为城市标帜的建筑是几座著名的教堂、宫殿、国家剧院,还有那使陌生人误以为教堂的蔚为壮观的市府大楼。但是形成一座城市整体风貌还要靠无数民宅和店铺。我非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说不出多少理论,只是凭直觉。试设想,那些精美无比的教堂被遮蔽在摩天大楼的森林中,那还是维也纳吗?市内还到处可见成群的百年以上老树。几百年高龄的老树在我国也不鲜见,但多在庙宇、皇宫、特定的园林内,作为文物保护对象,少见于城市沿街。此无他故,人家不干砍树建楼之事。
二
安顿住宿后第二天首先是访故居。我当年工作的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根据协议,维也纳像西柏林一样由四国占领,“世和”的秘书处就设在维也纳的苏占区。
我奉派到那里是在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或称“中立条约”)签订后一年,占领区已经撤销,各国军队也已撤退。但是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我们还是有不成文的纪律,不能擅自到处走动,所以活动范围还是基本上在前苏占区和“中立区”。所幸这个区内颇有一些著名的建筑,例如“中立条约”签字的地点——有“小凡尔赛”之称的“美景台(Belvedere)”、玛丽·黛雷丝女王时代建起的著名的“美泉宫(Shunbrunn)”以及著名的“州立公园”。


我首先想要寻找的是当年常去散步的州立公园和那里的施特劳斯雕像。没想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军纪念碑(或称“塔”,以其高故)。那是一座气度恢宏的建筑:碑本身已高耸入云,尖顶上又立一名高举红旗的战士,有刺破青天之势。底座由黑色大理石奠基,上面四扇硕大的凹面深红大理石镌刻着俄、德两种文字的金色铭文,开阔的广场周围圆柱游廊环抱,正面是一大片草地,不是平地而是徐徐向中间凹陷,像一个绿茵覆盖的大盆,别有情致。
这原是当地一景,确实气象非凡。在我访旧的目标中竟没有想起它,见到后略感意外。尽管苏联和东欧经历了剧变,维也纳人并没有拆毁这座纪念塔,他们尊重历史。不过幸好那上面是一名士兵,如果是领袖像,那就难免遭殃了。依稀记得当年布拉格的山坡上刻有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领袖浮雕头像,从艺术上看,远远望去也是一幅雄伟而别致的美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就被炸掉了。维也纳到处矗立的名人雕像是城市景色的组成部分,这红军纪念塔也融入其中,成为景色的一部分。
我继续前行,找到了雕满天使的拱形门下站着拉小提琴的施特劳斯像,依然那么潇洒,只是不知何时给镀上了一层金,远不如原来的石头本色来得亲切、朴实,维也纳人也未能免俗,令人遗憾。

州立公园中,除施特劳斯外,还有舒伯特和布鲁克纳两位作曲家、爱米尔·辛德勒(贝多芬的挚友,第一个为他写传的)、19世纪著名奥地利画家阿默灵和另一位不太著名的画家加农,以及对维也纳市奠基有功的市长泽林卡的像。维也纳不愧为文化名城,仅从名人故居和雕像之多, 保存之好,就可见一斑。
当年奥地利哈泼斯王朝以及奥匈帝国曾盛极一时,当然少不了帝王的遗迹和雕像,如玛丽·黛雷丝、佛朗索瓦·约瑟夫一世等。但是更多的是科学、艺术、学术、音乐大师的遗迹,诉说着几个世纪人文荟萃的辉煌。不言而喻,在此地住过并留下事迹的音乐家之多是举世无双的。

贝多芬的雕像也在此不远,地址就称“贝多芬广场”,人像是坐姿,底座一边雕着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另一边是许多带翅膀的小天使,二者象征着悲壮的奋斗和飞翔的音乐,可谓匠心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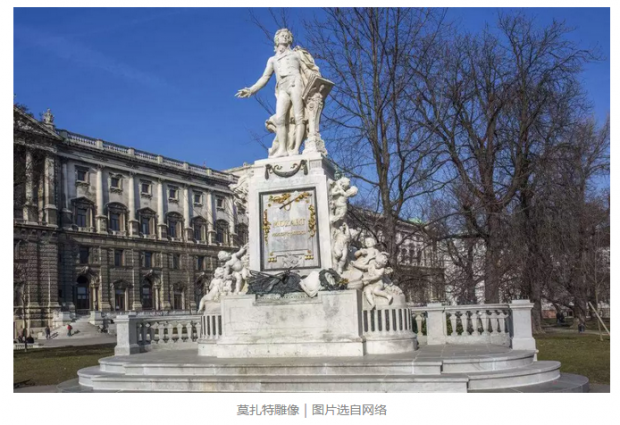
莫扎特更是这个城市的宠儿,他的故居、博物馆、以及雕像所在的公园都在同一区内。在一座旧王府内有纪念他的“费加罗室”,附近的小店还有以莫扎特命名的巧克力、饮料等等。此外海顿、勃拉姆斯都有纪念馆。这里只举我们熟悉的名人,当然远不止这些。
奥地利的君主有重视和延揽人才的传统,使维也纳成为18、19世纪欧洲学术文化重镇,除音乐、美术外,经济学、哲学都有“维也纳学派”。不论原籍哪国,凡在此地生活过一段时期,进行过学术和创作活动的,维也纳都予以认同,纳入自己的宽广的怀抱,以不同方式留下他们的痕迹。所以许多雕像、故居、纪念馆不一定是奥地利名人,来自欧洲各国的都有,只不过标明此人某年到某年在此居住或工作。他山之石都是维也纳的骄傲。
三
我的旧居离州立公园不远,我本来就不认路,事隔多年更说不上哪条街模样熟悉,因为“春来遍是桃花水”,到处是窄窄的石板路小街、路边几家小巧玲珑的咖啡馆、门外花草簇拥的护栏围起几张露天雅座,都似曾相识。不能跟着感觉走,只能拿着地图根据确切的地址按图索骥,还问了几个行人。
忽见一块路牌赫然写着“Möllwaldplatze”,眼睛为之一亮,终于找到了!所谓“platze ”是中东欧城市常见的结构,即街边凹进一块方地,三面房舍呈马蹄形,可大可小。在我们这里就称“广场”了,人家并无夸大为“广”的意思。当年“世和”把这三面的楼都包了下来,一面做办公室,另外两面作各国员工宿舍。
中国和苏联一样,有政府的力量,比较阔气,自己买下了当中一栋的二、三层楼连同阁楼(当地的叫法:一楼称底层,二楼另有名称,三楼称二楼,所以这栋房子连同阁楼实际有五层,我们占上面三层),作为工作人员宿舍兼会客室。3号门牌、老式厚重镶玻璃的大门,一切依旧。
当然今日此门中已经物是人非。可惜大门紧闭,不见任何人出入。否则,奥地利人比较热情友好,如能见到主人,说明情况,也说不定能允许进去看一眼。我只能在门前摄影留念,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由于我们只有一周的时间,只参观了贝多芬、莫扎特和弗洛依德的故居兼博物馆。这些故居就在普通民宅之中,占一套公寓,其余各层都住着普通人家,关起门来互不干扰。故居门口挂着不太醒目的标帜,也像是一家人家,有的开着门,有的需要按铃进去。不过一进门就景象不同,当门有售票的柜台,有各种说明书、小册子,弗洛依德的故居还有一小间书架,出售他的以及有关他的学术著作。面积虽然不大,陈列品却很丰富,房屋大小可以看出当年主人的生活状况,就这点而言,贝多芬的最窄小,莫氏和弗氏都有十几间房间。两位音乐家故居进门第一间屋都有一台特殊的音响设施,摆了几副耳机,有一个键盘,带上耳机随便按一个键盘就可以听到一首曲子,好像有9种选择。这大概已经是各种音乐博物馆的必备设施。如果观众愿意,可以一直听下去,无人干涉。不过大约很少人专门到此地来听音乐的。
弗洛依德故居则除了有关文物事迹外,还有一间屋子,有一台电脑和大屏幕,根据说明,可以进入电脑程序,依照弗氏学说自己进行心理测试,或咨讯一些问题。看起来很复杂,我没有试,也没有看到他人试用。在弗氏故居除了一般的参观者外,还遇到一群学生,围一圈席地而坐,有一位大概是老师在那里讲解。
除了正式的博物馆之外,这种规模不大而内容丰富的故居兼博物馆在维也纳不知凡几,散落于寻常百姓家,同时得到很好的维护和管理,日复一日地向一代一代普通人传播知识,延续着一脉书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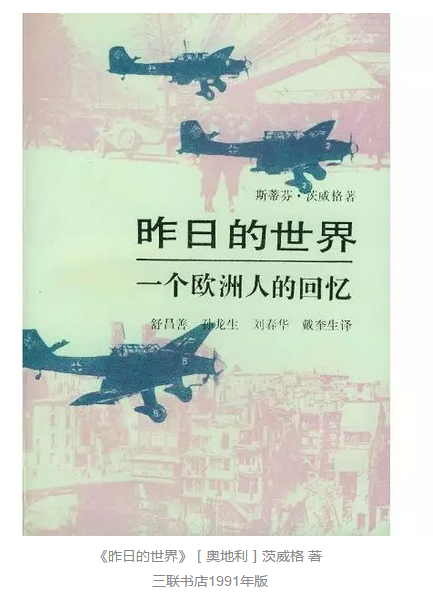
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著《昨日的世界》,描述直到第一次欧战爆发之前这座令人神往的人文之都:扫房女仆因一位著名歌剧女高音去世而泪流满面;一个学童有幸被勃拉姆斯摸了一下头而得意非凡,令所有同学都羡慕不已。那是怎样一个全民尊重和欣赏文化知识的时代!茨威格经历过这样时代的欧洲,又亲见其两次被残酷地摧毁,黄钟委地,瓦釜雷鸣,自己也一起受难,被迫流落美洲,我似乎对他最终自杀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无端想起了王国维的“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挽诗)。茨威格如能见到今天维也纳所延续的文化气息会略感欣慰呢,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仍不免失落?
四
与文化气息浓厚相对的印象是商业气息比较淡。西方许多国家的首都都不是热闹的工商业城市,例如瑞士的伯尔尼、荷兰的海牙等,很难比较。我是从北京去,所以只是相对于已经习惯的北京的环境而言。
首先广告牌少得多,大街小巷很少见到那种刺目的、无法躲避的大广告牌。既然没有大高楼,也就没有那种像头顶疮疤一般的屋顶广告。公共汽车和电车外壳干干净净,未见刷广告的。维也纳街市的特点是小店多,大店少,除了散于居民点卖日常食用品的联锁超市外,最多是小专卖点,例如鞋子、男服、女服、儿童服装、外衣、内衣,都是分开的,几乎没有见到大百货公司。当然我没有去“联合国城”,不知那个现代化的市区情况如何。这样对购物确有不方便处,要多跑不少路。
市内有一条著名的“走街”,不能通车,比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都要窄而长,并且是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店铺,但是仍然不使人感到浓厚的商业气,因为每一家小店的橱窗布置各有特色,浑似艺术展览。卖瓷器、玩具、珠宝等店铺的橱窗固然可以精心布置,争奇斗艳,就是日常用品锅碗瓢盆的橱窗也十分雅致。如一切商店一样,打折销售的标牌随处可见,但大多放在适当的地位,不破坏橱窗的美感。只是偶然看看标价,却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在这里逛商业街权当是游画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是一次精神的享受。
这条街上原来还有一棵有名的“诗树”,任何人写了诗都可贴在上面,路人读了,喜欢哪一首,就可以把纸条揭下来收藏。如果纸上有作者名字和联络方式,还可以就此以诗会友。至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老伴来访时还曾见到这棵贴满纸条的树,但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找到。行色匆匆,也未及细访,不知这一可爱的习俗是否还在继续。
另一点令人愉快的是维也纳汽车比较少,还未遇到过堵车。公交十分便捷。电车轨道在马路中间,刚好隔开汽车上下道,除了大道的十字路口由红绿灯控制外,从小街驶出的汽车都自动让电车和行人。电车到站时,两旁汽车也自动暂停,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穿马路上车。我基本上没有见到可以招手停下的出租车,在闹市地区有集中的出租车站。
说面貌依旧,那是外壳。无论是民宅还是公共建筑,内部的设施一直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如卫生设备、供水、供暖系统、厨房设施、下水道等等,至今“现代化”工程大约只完成了全市居民住宅的一半。有不少住宅没有自用浴室,甚至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中央供暖更待普及。历届市政府的工作计划中都有继续改造内部设施的预算和任务。
有一项“旧貌”令我惊讶的是电线都暴露在外,从房屋内引出的电话线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危险,没有想到在这点上,维也纳竟是如此落后。而北京差不多十年以前就开始把电线埋入地下。
我无意拿北京做比较。尽人皆知的过去的失误已经无法回头。也不能要求北京像历经数百年发展成熟的维也纳那样维持“不变”。况且早已有不少人指出,欧洲古建筑是石结构较多,框架既易于保存,内部也容易改造,这是比中国的老房子的优越性。
当然还有一个基本条件是城市人口密度不大,试想在北京或上海,汽车如在公交车站旁暂停一分钟,会出现怎样的堵车长龙?维也纳人口自第一次欧战以来减少很多,1910年有210万,现在已不到150万,而且下降趋势尚未停止,因此解决老龄人口的需求是市政中一个重点问题。
奥地利未来发展如何,不属于我这他乡游客操心之事,我只是感受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典雅的氛围。这点,老北京原来不缺而现在已破坏殆尽。至少维也纳人提供了一种在炫富比阔、开私车、穿名牌、大嚼生猛海鲜以外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本文首发于2004年)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